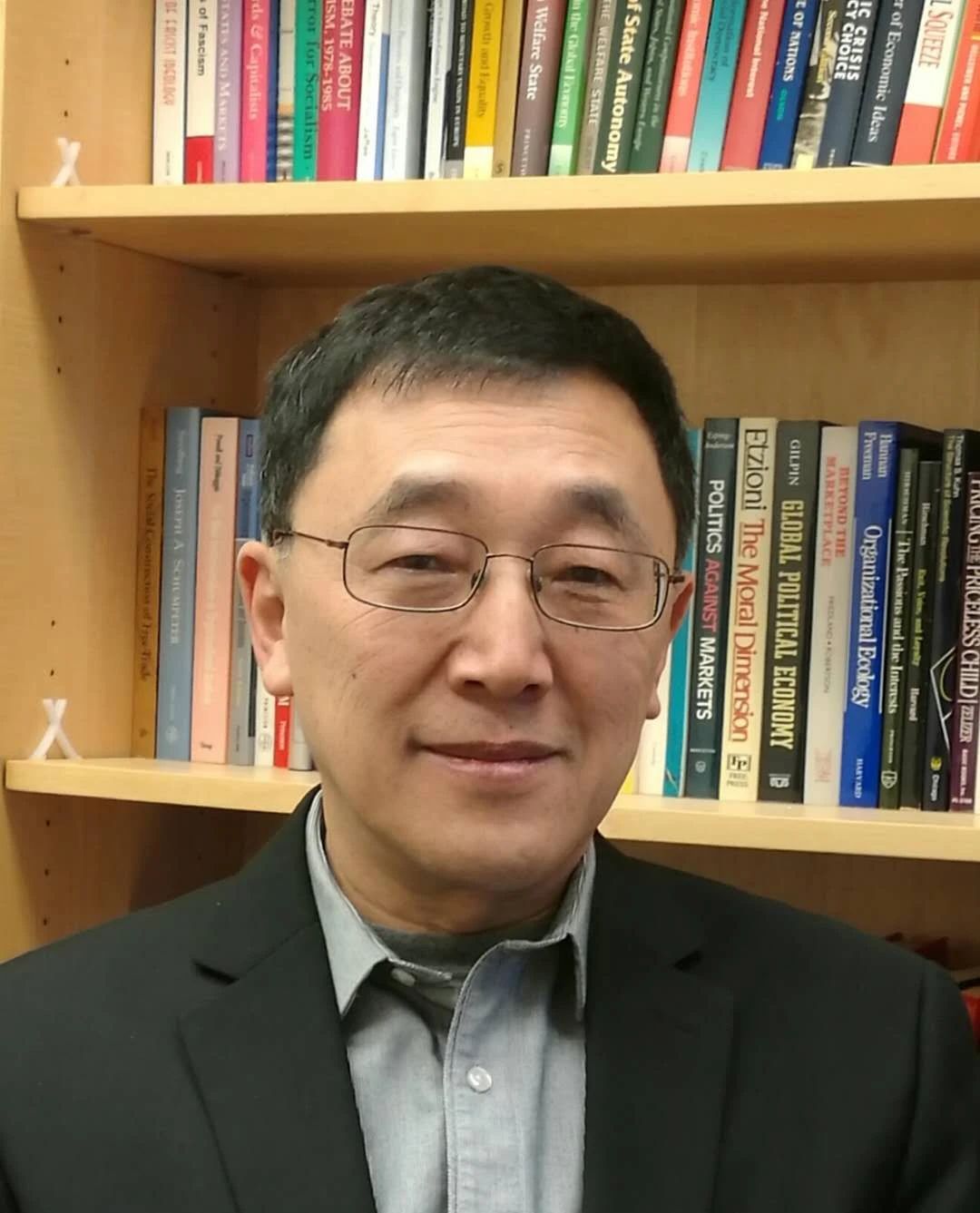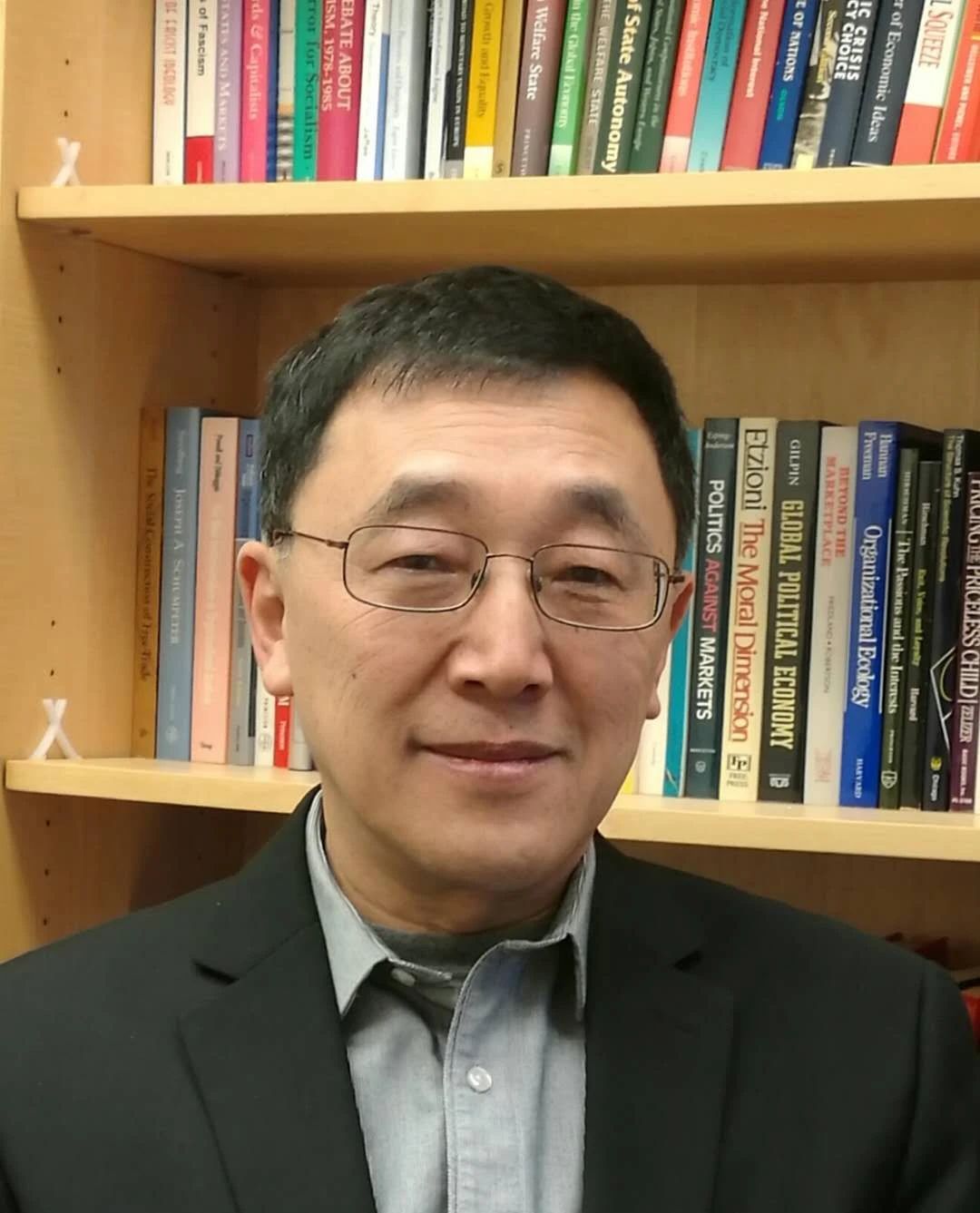
*来源:北京大学教育学院(ID:pkugse),作者:高柏
我在1983年9月至1986年1月期间在北大高教所读硕士学位。这两年半是我人生之路的交汇点和转折点。在那里我放弃了之前的文学理想,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并开始国际研究这一生的职业。在高教所的这段经历对我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与其说是来自高教所本身,不如说是来自北大,来自许多校友心目中母校的那个黄金时代。
我是1983年7月从北大东语系日语专业本科毕业后到当时的高等教育研究室读硕士的。在此之前,我一直想成为一名文学翻译。
我学日语的机缘与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命运有紧密联系。
我于1971年1月初中毕业。当时哈尔滨的高中都关掉了,我们只好在家里待业。这一年的7月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结束时两国政府同时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问中国。这件事情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因人而异、因地而异,但是它对我的影响却很快就显示出来,并成为我后来人生轨迹的原点。
1972年春尼克松访华后,中国的城市掀起了一个学习外语的浪潮。等同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我开始自学日语。父亲早年留学日本,家里有“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中日对照的《日语会话》和《科技日语读本》。这本《日语会话》的内容是各种接待外宾情景下的对话,这对一个身处“文化大革命”漩涡、周边是一片混乱的少年有莫大的吸引力。从小学开始,每当我没书读的时候,都会拿出这本《日语会话》把中文部分再读一遍充饥。开始学日语后,我很快就把父亲的那本《科技日语读本》从头学到了尾。后来在北京中科院工作的二姨给我邮来了一套三大本油印版的北大日语专业一年级工农兵学员的教材,这成了我每天抱着看的宝贝。到了1973年5月下乡的时候,我已经把日语语法基本自学了一遍。
1973年秋季,哈尔滨开始了英语广播课程。我和下乡所在的省农业机械化研究所附属农场的几个小伙伴又开始跟着收音机学英语,有问题就去请教研究所里一个会4门外语的“右派”。再后来,哈尔滨的外文书店已经可以买到《英语900句》和《灵格风》。我当时学英语试过几套教材,虽然没有学完其中的任何一套,但是对外国的兴趣却与日俱增。
下乡的第二年发生了一件冥冥中与我后来上北大、研究日本、留学美国以及一直从事社会科学并研究国际问题有强烈关联的事情。
1974年春天,农场接到通知派人参加哈尔滨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函授大学辅导员培训班。我们农场把这个任务派给了我。一去市里听课,发现主题是第一次石油危机带来的国际形势变化。因为学着两门外语,我对这个题目十分感兴趣。由于表现突出,第一期辅导班结束后,我从学生变成了给第二期学员上课的兼职教员。从那时起我似乎就命里注定这辈子要当老师。
那一年秋天,农场又收到另外一个通知,派人参加在黑龙江省图书馆由黑龙江大学的熊映梧教授主讲的《资本论》原著学习班。我在这个学习班为期一年每星期一次的学习中,打下的政治经济学的底子后来可是管大用了,不仅在应付高考、北大本科的政治课以及北大考研究生时基本不用花时间复习,就是后来在普林斯顿读博士时也省了许多阅读时间。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我只上过初中,而且上初中的三年里有两年在挖防空洞,可以说连初中文化都没有。这两个学习班实际上是给我一个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它们是我被“文化大革命”荒废了6年后仍然可以考上北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后来的许多年里,我一直对第一个学习班感到不可思议: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在黑龙江这样山高皇帝远、生活节奏似乎一直比时代潮流慢几拍、很少有老百姓关心政治的地方,1974年居然有人想起来要给一帮下乡知识青年办学习班,讲石油危机给国际经济秩序带来的变化。我人生道路的原点是1971年中美关系发生变化后开始学外语,但是只有在这个学习班的经历才真正地奠定了我这辈子与国际事务研究的不解之缘。多年后,我读到一段关于70年代初中共党内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历史,才知道当时党内委托陈云研究国际问题,他率领人研究的结果发现:1973—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的一个重要后果是结束了发达国家战后长达20多年的黄金增长期,发达国家已经失去投资机会,国际上过剩的游资正在发展中国家到处寻找新的投资机会。这正是后来中国对外开放的逻辑起点。
1977年秋季我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进了哈尔滨机械工业学校。在校期间国家恢复了高考,我上书教育部要求参加,被告知应该读完参加工作两年后才有资格。毕业后我在哈尔滨市松江拖拉机厂工作了一年后,于1979年经厂里批准提前一年参加了高考。
当时我决定报考日语专业。因为我的日语完全是自学,根本没有口语能力和听力,加上1979年一类院校日语专业在黑龙江只有五个名额,一个北大,两个吉大,两个上外,我第一轮的第一志愿报的是吉大,第二志愿是上外,第三志愿才是北大。结果一发榜,由于77、78两届高考把非应届生里的能人全招走了,我居然混了个省文科状元。1979年的黑龙江高考与前两次不同,这次由于考生报的院校偏低,招生办允许考生在公布分数后改志愿。当时市招生办主任是我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函授大学时老师的老公,他告诉我,我选任何大学的任何文科专业都能去,他建议我选北大的国际法。但是我当时的理想是文学,我坚持去日语专业,只把第一志愿改成了北大。
我们读北大本科的那几年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每天早晨五点开始校园里就有许多人背外语,各种讲座都是人山人海,每个人似乎都想把过去耽误的时间全补回来。
在北大日语专业本科的前三年我一直做的是文学梦。上学期间翻译了三篇日本小说在杂志上发表,挣了近700元的稿费。当时给我们上课的那些工农兵学员老师每月工资只有50多元,我一下子成了土豪。当时北大书店卖的新翻译的外国小说我一概不问价格就买下来,四年里攒了50多本。到了第四年为毕业后出路着想时被告知,要想做一个专业的全职文学翻译几乎不可能,因为这样的职位全中国满打满算也没有几个。仗着下乡时国际研究和资本论的背景,我决定报考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经济方向的硕士,并且开始做各种准备。
1982年年底时,日语教研室的领导来找我,告诉我北大高等教育研究室想招收会日语的硕士生,并说如果有兴趣可以找汪老师谈一下。
继续留在北大校园里读书对我当然很有诱惑力。我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夜去汪老师家见面,一谈就谈了三个多小时。汪老师介绍说他和郝克明老师正在承担一个国家“六五”重点项目,主要研究高等教育结构如何为国家现代化服务。之所以要招学外语的学生,是想通过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进行横向比较,以便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他告诉我北大的高等教育研究未来一定是跨学科的,让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人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来研究高等教育。汪老师反复用日本留学的机会来诱惑我,说只要你来读我会通过当时任驻日使馆教育参赞的彭家声老师为你找机会,保证你在两年半的学习期间去日本一年到一年半。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我直接告诉他硕士期间我不想出去,我想先坐上三年的冷板凳,对中国高等教育有一个基本了解之后再出去有针对性地读博士。那时候的出国机会十分稀缺,与今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碰到一个留学机会送上门都不要的学生,汪老师喜出望外,与我约定读完硕士留校,然后找机会出国读博士。我与汪老师那次夜谈达成的这个约定是后来我一毕业留校他就同意我马上出国读博士的直接原因。
等我们1983年秋季入学不久,高等教育研究室就升格成高等教育研究所。我在北大的七年期间,读硕士和后来留校加一起这三年与本科四年的体验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高教所这三年的感觉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如鱼得水。
首先是与同学间的跨学科交流成为我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当时汪老师已经出任北大教务长,我们除了上课几乎见不到他。他也对我们实行放养,没有太多的约束。83级的北大各专业研究生全都住在34楼,对跨学科交流十分有利。很快我就加入了未名学社。这个学社由当时北大研究生会学习部的成员建立,其主要成员先后有马伯强、王培、李明德、罗健平、陈坡、吴国盛、钱立、孙勇平、孙来祥、顾昕、张炳九、李书磊和黄永山。我们经常在一起就各个专业领域的论题侃大山,也经常请人来讲。与本科期间同学间的交流只限于本专业不同,研究生期间的横向交流十分频繁。这成了我学习其他领域知识、开阔学术视野的好机会。
其次是我们不仅是在学习各种有关高等教育的理论,而且还有机会去设想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我直接负责了北大研究生会与哈工大研究生会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共同举办的1984年全国研究生高等教育改革研讨会的筹备工作。当时北大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许多同学准备了文章。我们在未名学社不仅进行了多次讨论,而且最后每个人的稿子都集体过了一遍。听这些同学从不同专业的视角讲他们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看法,对我这个学习高等教育的来说,无疑是一次次的头脑风暴。在这次研讨会上,我们有机会与来自全国各高校的研究生交流,看到各种活跃的思想火花,使我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也正是通过准备这次会议的发言,开始形成对各国高等教育模式及其背后成因的兴趣。
1985年4月,我又有机会作为大会的会务人员参加了在香山举办的中日大学校长会议。当时丁石孙校长是中方代表团团长,由北大承担会务。我的任务是收集日方的校长们。后来我根据收集的内容把日方大学校长们关于如何办大学的观点整理成一篇文章发表。
在高教所写硕士论文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成长过程。其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我开始接触制度学派的理论并成为一名笃信者。由于在北大参加未名学社的活动,我对为论文跨学科寻找各种能用得上的理论有极大的热情。在这个过程中我读到了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那本关于高等教育系统的名著。当时感觉他把高等教育视为一个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互动的子系统,寻找高等教育变迁之外部动力的视角十分有用。于是我把它与日本高等教育的历史结合,发展出一个硕士论文的分析框架。论文初稿写成后给汪老师看,他说你这个思路能广泛适用。由于这段经历,我后来联系伯顿·克拉克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简称UCLA)教育学院读博士时就变得很简单,只把我硕士论文的内容介绍了一番,既没考托福,也没考GRE就被录取了。等后来到了普林斯顿学社会学后,才知道伯顿·克拉克是旧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课上的阅读材料里仍然可以见到他的名字。当时普林斯顿正在成为美国社会学新制度学派的重镇之一,我在那里受到了一个新制度学派的训练。
第二,我一改过去不喜欢历史的毛病,开始追求理论的逻辑必须与历史的逻辑相一致的原则。我上北大本科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当时与许多学生一样认为中国的历史对中华民族寻找未来之路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在北大本科期间我对上历史有关的课一直兴趣不大。领了汪老师给的研究任务后,我广泛阅读有关日本高等教育历史的有关文献,发现不懂历史还真就无法解释日本高等教育结构的变迁。我做论文研究的第一步是找出日本高等教育1880—1980年各个专业入学的统计数字,然后找出其迅速变化的时期,再从历史上这些时期发生的政治经济社会事件中去寻找推动高等教育结构变化的原因并将其概念化。当时上汪老师高等教育史这门课时对其内容的博大精深甚为叹服,但是与此同时也隐隐感觉我最感兴趣的并不是历史细节本身,而是各国高等教育模式之间异同背后的深层原因。到了美国学习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后,对历史学与历史社会学之间的区别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前者更多地关注历史本身的细节,而历史社会学则是从历史的逻辑中建构解释变量和分析框架。这是我后来在研究中一直实践的。
第三,我开始养成在科研中挑战主流理论的习惯。我硕士论文得出的结果与汪老师当初告诉我的这个国家重点项目的立意是相悖的。他最初向我介绍这个项目时的思路是,为了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我们应该如何调整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并试图通过分析发达国家是如何做的,找到可供中国借鉴的经验。然而,我在做论文的过程中通过分析日本高等教育结构在1880—1980年这100年间的发展过程时发现,日本高等教育结构发生的很多重大变化,特别是文科的发展,并不能从这种偏经济的视角来解释。明治维新后日本设立东京帝国大学时的主要目的与其是受发展经济的驱动,不如说是受建设现代国家机器的驱动更为贴切。而20世纪第二个十年,日本大正民主时期文科的迅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妇女解放运动产生的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其影响远远大于经济的影响。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工科教育也始终未达到像中国那样的规模。汪老师看完初稿,说这是你论文最重要的发现。由于这段经历,后来我在研究日本经济时无论选择什么题目,总是从如何用日本经验的特殊性挑战西方的主流理论出发。
硕士毕业后我们未名学社的成员大部分留校,钱立还当上了丁石孙校长的秘书。当时的校团委书记、丁校长的博士生张来武把我们这几个青年教师招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校长智囊团。丁校长专门与我们见面,鼓励我们为北大的未来出谋划策。在这段时间里,我把上汪老师高等教育史时发展出来的特殊兴趣派上了用场。上汪老师课时我最为关注的是各国高等教育的模式以及这种模式与该国政治经济社会因素之间的深层关系,像日本和法国模式代表的为建设现代国家机器培养公务员的模式、德国重视科学研究的模式、美国重视社区服务的模式、英国重视通识教育的模式以及苏联重视各种工程类专业大学的模式等等。在我们关于北大未来发展模式的讨论中,我一直认为北大应该办成一个哈佛与东大的合体,既是一个出新思想和新学术成果、引领风气之先的研究重镇,也应该是培养现代国家管理人才的教育基地。
当时联系出国的过程很顺利,得到UCLA教育学院的录取后又考上了北大的出国教师英语进修班。留校后的1986年春季学期基本上是在这个进修班度过的。同年9月赴美,开始了求学之路。
转眼间40年过去了,当年的高教所如今已经发展成教育学院,汪老师已经驾鹤西去,无论北大的校园和氛围,还是中国与世界的格局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对当年在北大学习时的种种回忆至今仍然经常把我带回那段令人难忘的岁月,那个我人生之路的交汇点和转折点。
高柏,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3年于北大东语系日语专业毕业后成为高教所第一届硕士生,1986年1月毕业留在高教所工作,并于1986年9月赴美。1994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1993年7月开始在杜克大学任教至今。
原文刊载于《学术之道》,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作者高柏。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2、芥末堆不接受通过公关费、车马费等任何形式发布失实文章,只呈现有价值的内容给读者;
3、如果你也从事教育,并希望被芥末堆报道,请您 填写信息告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