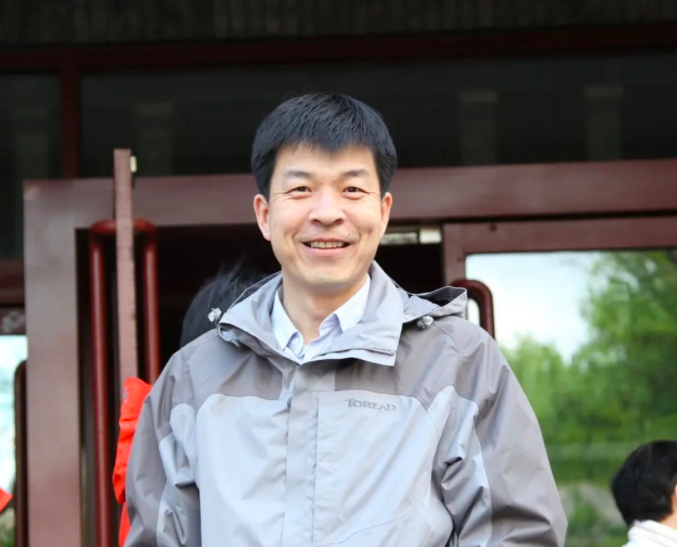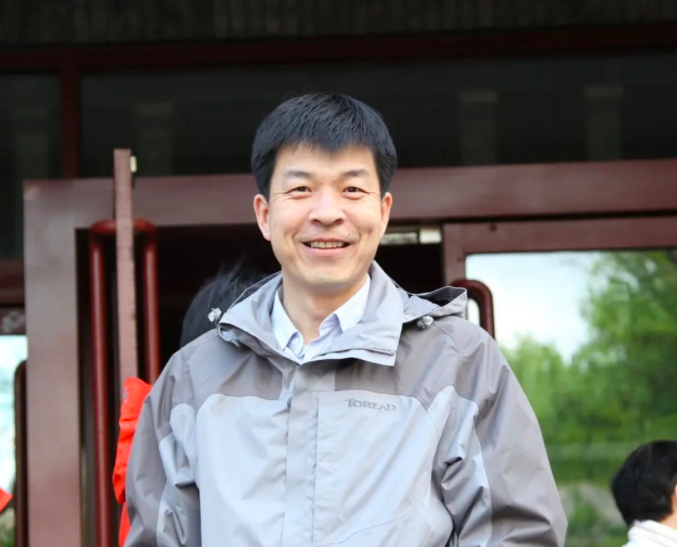
陈晓宇,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来源:北京大学教育学院(ID:pkugse),作者:陈晓宇
一
我开始学习教育是在1990年。那年我从北大计算机系本科毕业,原本计划参加的研究生招生考试被取消了,改为全部通过推荐免试录取。听同学说有个高教所在招研究生,而且不限专业,我就去报了名。
面试是在电教楼四层顶头的一间办公室里进行的,参加面试的只有我一个人,面试老师是汪永铨老师和闵维方老师两人。在问过了一些基本信息和原专业的学习情况之后,汪老师问了唯一一个有关教育的问题:“你对教育有什么看法?”虽然之前的专业与教育的距离很远,但在准备面试时我也多少做了些思想准备,打算从自己的教育经历、听到的社会上关于教育的一些讨论来说自己对教育学的志趣和认识,不过现场在两位老师平静关注的目光下,我脑子一片空白,一张嘴就卡了壳,在尝试了几次之后也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最后老实坦白道:其实我只是想上研究生,之前没有涉猎过教育,对教育没有看法。听到这个回答之后两位老师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汪老师对我说:你报我们吧,我们录取你。我就这样进了高教所。
进入一个新的学习阶段,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新的课程,新的环境,新的人。各个方面都让我觉得很开眼界。
首先是高教所学生人数很少,我们90级的硕士生只有三人(王蓉、刘国权和我),前面两个年级加起来也只有四人,这几个年级同学一起上课时,老师和同学围坐在资料室的阅览桌旁就够了;其次,即使是我们寥寥的这几个人,本科的专业背景也是五花八门,学文学理学工的都有。学习内容、课程形式的开放性是我之前学习过程中没有经历过的。记得第一学年汪永铨老师开了一门两个学期的“高等教育系统”课,算是给我们这些大多数没有教育专业基础的同学的一门引论课。这门课的第一个内容是“教育”的概念,然后是讲“系统”“环境”“要素”等概念,单这几个概念就足足讲了两个多月。汪老师本身也是理科出身,我们一起上课的同学在私底下经常赞叹他讲课的深度、广度还有内容的逻辑性。老先生在探讨问题的时候总是把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介绍给我们,有时候会说他自己的看法,但对不同观点似乎也并不做太多褒贬。还有一个比较深的印象是我们眼里的权威泰斗老先生,在课上以及课下跟同学交流的时候,经常会说“这个我不懂”“这个我不明白”这样的话。记得有一次上课讲到教育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说到教育中理论与实际脱离的问题,课间休息时我跟汪老师说,在教育领域理论结合实践特别难,是不是有人本来就认为理论不应该跟实践结合呢?汪老师先是稍愣了一下,之后想了想,微笑着缓缓地说:“你这个想法有意思啊,我还真没有想过。”也是在这门课上,我第一次了解到关于教育和高等教育,存在着“研究领域论”和“学科论”两类不同的观点。
闵维方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门课是第二学期的“组织理论与高教管理”。闵老师当时从美国留学刚回国不久,跟陈章良、曾毅并列为北大最受关注的三位海归明星教师,他的课堂上除了高教所的研究生之外,还有管理科学中心的研究生,这门课也是他们的必修课,不过对他们来说课的名称有所不同,叫“组织理论与管理原理”。另外还有一些青年教师也在一起旁听。闵老师的课是用英语讲的,虽然其中有些时候,主要是跟学生互动时,会用中文,但课堂语言主要是英语。这是我第一次听英语讲授的专业课,感觉还是有些吃力。这门课是在哲学楼的教室上的,上课时间是在下午,有一次上课时外边天气特别好,闵老师就临时商量把那节课改在户外上。他让人去买来一箱汽水,大家在图书馆草坪的一棵白皮松下,围着闵老师坐在草坪上一边喝着汽水,享受着燕园里的空气和阳光,一边听闵老师富有激情地侃侃而谈。过了这么多年那节课讲的内容早就不记得了,但在草坪上上课这事直到现在我们同学聚会还会一起回忆起来。
闵老师来到高教所支撑起了一个新兴的学科,也带回来教育经济学的数量化研究方法和工具。据说当时北大老师中用的最新版的社会科学统计软件SPSS,都是从闵老师处拷贝的。闵老师1990年发表了一篇中国高校规模效益的论文,证明了在中国高校中的规模经济现象,提出中国高等教育要挖掘当时高校的内部潜力,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在当时学术界和管理层中影响很大。后来主管教育的李岚清据说很重视这件事,坚持扩大高校的规模而不增加高校数量,结果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高校的数量基本维持不变,甚至还有所减少。

我硕士学习的专业是叫高等教育学,拿的学位也还是教育学学位。尽管如此,我入学的时候已经明确是学习教育经济与管理方向,而且我之前已经有一届同学是这样招进来的。经济学和量化研究方法成为我们学习中重点强调的。当时高教所自己还没有开设这些课的能力,所以我们去学了一些外系甚至外校的课程。我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SPSS课是在心理系上的,授课老师是王登峰;我的微观经济学是在管理中心上的,授课老师是王为民。
我入学一段时间之后,有一次闵老师问我学习的感受,问我学习中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说了自己的一个担忧,就是不清楚我们强调的这种量化的研究方法在教育领域有没有前途。因为当时听老师和同学讲,国内一些学者对北大高教所的学术方向和特点存在一些议论,也有一些不同看法,比如这样的研究只有方法没有理论,研究的问题不是教育的核心问题,而是教育的外部现象,等等。闵老师听了后对我说,事物都有质和量两种规定性,从量的角度做研究肯定是一个长远的方向。就是这样一句简单的点拨,让我感觉茅塞顿开,用当时老师们的话说是坚定了自己的专业思想。我之后经常跟同学朋友们说,闵老师就是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
我们的教育经济学的课是魏新老师讲的,他那时候还是北京科技大学高教所的老师,所以我们要每天早上从北大到钢院去上课。那门课是在秋季学期上的,有一段时间一大早骑自行车去上课特别冷,到教室里大家都冻得手脚发木。在这门课上魏老师给大家留的一个作业是翻译当时世界银行出版的Education for Development,每人翻一章,我领到的是第七章教育成本(TheCost of Education),翻完之后还在课堂上做了交流,我记得还得到了魏老师的表扬。在我之后学习和工作的二十几年里,自己的研究一直围绕教育的成本、收益和教育财政展开,现在回想起来,不知道有多大程度是受这门课和这次作业的影响。
在我做硕士论文期间,把硕士论文的主要内容缩写成一篇文章,参加了北大第一届挑战杯,我记得论文的题目是“中国高等教育内部效益研究”;当年比我低一年级的官风华也一起参赛,他的论文题目是“高等教育中的搭便车现象”。我们两人的论文都得了当时的挑战杯一等奖。我后来看到了评委对我论文的评语,评语的结论是:这是一篇较高质量的论文。那笔迹一看就是汪老师的字。看到这个评价我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因为之前听到汪老师跟所里老师们聊天时说过,他评议成果写评语的时候,会区别所评的是“文章”,还是“论文”。在他眼里,有的东西,就是在“做文章”,而正经的研究成果,才是“论文”。
那时魏新老师已经调到了北大高教所工作,当时高教所在围绕闵老师配备队伍,魏新老师,还有当时我们的班主任、青年教师马清华老师常常到我们宿舍来跟学生们聊天。1993年我硕士毕业之前,有一次魏老师找我谈话劝我留校,我当时就答应了。就这样没有多想,没有纠结,就开始了教育研究的职业生涯。
很多年以后才认识到,学生在学习生涯中总是要面临新的环境、新的内容,作为学生也许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老师的行为和安排就是事情原本的样子。但对创造这些新鲜环境的人,对当时的老师来说,他们其实也是在当时的条件限制下,做各种创新的探索和尝试。高教所当时人少规模小,北大本身没有教育本科专业,所以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来源于各种不同专业(记得后来高教所招收硕士研究生时明文规定,报考高教所的考生可以选择高教所单独命题的试卷,也可以选择采用北大任何其他专业的研究生考试试卷,只要成绩合格都可以获得复试资格)。师生背景的多样化让北大的教育学科自然更加开放,呈现出多学科跨学科的特点。
二
我刚参加工作就加入了闵老师领导的一系列世界银行的项目。在世界银行支持的第一个中国贫困省教育发展项目中,闵老师最初是作为世界银行的代表进行项目设计论证,之后成为中方专家组的组长,负责对项目实施进行监控检查和咨询指导。贫一项目包括山西、陕西、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六个省份,110多个项目县和19所项目高校。从1993年开始,高教所承担了世界项目下的中方专家组秘书处、高教评估和重读辍学这三个课题。三个课题的经费一共有一百多万元,这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一个文科单位来说,是一笔相当巨额的经费了,也改变了高教所一直以来的拮据状况(时常高教所的前辈老师们忆苦思甜,说之前高教所经费紧张的时候,曾为了给所里老师发奖金而专门向学校财务处打报告借过140元钱)。
我开始工作正赶上这些课题的开展。我个人介入比较多的是中方专家组和高教评估项目。中方专家组由闵老师任组长,成员还包括北大的陈良焜、北师大的王善迈、北航的冯厚植、北京八中的温寒江,还有山西省教委的张增智。中方专家组每年要去项目省进行两次考察,每次一般为时两周,考察两个项目省,考察完之后撰写考察报告提交给教育部和世界银行。一般情况下来到一个项目省,会考察两三个县和两三所高校,考察项目设备购置和使用、基建项目的进展和质量,与教育部门和学校的管理人员、一线老师进行座谈。回顾起来,通过这些考察工作我自己收获颇多,一是对贫困地区各级学校以及区域教育的运行和管理有了一些具体了解,有机会与几位资深专家共处共事学到了东西,还有就是也好好地领略了偏远山区的美景。高教评估项目的负责人是魏新老师,主要的项目任务是基于项目高校提交的年度报告和实地考察情况综合成为总体的年度报告,提交教育部和世界银行。这些项目单位尤其是基层的项目县和项目高校,大都是第一次接受在当时算是很大金额的援助项目,所以对项目的工作普遍特别认真。项目中存在的一个共性的问题是,项目单位最初的设计方案中确定的目标是通过项目实施来提高办学效益,其中降低生均成本这一项普遍没能实现,各个项目单位都有这个情况。专家组了解之后通过书面报告和当面汇报等形式,数次向教育部和世界银行反馈,分析说项目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增加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势必会导致生均成本上升,但此时的办学质量与经费短缺情况下相比也有提高,因此生均成本增加并不意味着办学效益降低。世界银行和教育部也都理解和接受了专家组的意见,此后在项目的评估检查中将生均成本仅作为参考指标而非硬性要求。

前一两次的专家组和高教评估的报告都是魏新老师主笔,之后几年就是我参照之前的体例内容来写了。回想那个时候课题组的人手不多,每个人承担的工作任务相当多,每天很忙也很充实,晚上在办公室加班赶文件是家常便饭。闵老师很关心我的工作状况,他曾经对我说过,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工作任务重一些、有挑战一些,对年轻人的成长是有益的。他说,相反,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如果你有几年时间只给他发工资不让他干活,他就会被毁掉。这话后来我也经常会给新参加工作的同事们说。
三
我入学的时候高教所的位置在电教楼南侧四楼的东头,有一个资料室和一间阅览室(多数的课都是在阅览室里上的),办公室只有一个套间加一个单间。就在我刚刚参加工作前后,高教所增加了几间办公室。因为我本科学习计算机的背景,闵老师安排我负责用他领导的世界银行贫困省教育发展项目的课题经费购置了几台电脑,并在一间办公室里为高教所建设一个计算机房。20世纪90年代初互联网在北大校园里还是个很新鲜的东西,电教楼四楼西边的属于电教的计算机房刚刚连上了互联网,网线正好从高教所办公室的门前经过。当时在高教所访学的一位澳大利亚学者曾从网线下面跨一大步站到我们办公室门口,然后对我说:你们和世界之间的距离还差这么远。后来几经争取,北大计算中心终于在路过高教所门口的网线上加接了一个收发器,使高教所的一台电脑联网,并在北大计算中心为高教所开设了一个电子邮件账户。电子邮件是那时的新概念,我们认为电子邮件跟电话号码是类似的,可以是一个单位开设一个。最初的这个账户名称叫hedu@pku.edu.cn。(后来我又费了牛劲在一台Compaq服务器上装了一套SCO Unix,做高教所自己的邮件服务器,主机名叫hedu.pku.edu.cn,开始给老师们开设个人邮件账号,邮件账户名称我给大家建议都用名字简拼加姓的全拼,比如我自己的就叫xychen@hedu.pku.edu.cn,闵老师的就叫wfmin@hedu.pku.edu.cn。学生们的就是st01、st02这样排下去,当时每年招生4、5人,用两位数字来命名学生的户头,足够用了。)
我也自然成了负责用这个电邮地址对外联络的人。早期在用这个邮件账号收发的为数并不是很多的邮件中,就有跟陈向明老师最早的联络信息。当时闵老师告诉我说有一位从哈佛大学毕业的陈向明会回国到高教所工作,让我跟她联系一些具体的事情。其中有一件挺重要的就是关于陈向明老师住房的安排。经过所里领导的争取,北大同意在新建的燕北园教师住房中给陈向明老师分配一套两居室,闵老师让我把这个消息通过电子邮件通知了陈向明。后来在向明就要回国时,我跟她联系说她回来需要先在招待所住一段时间,因为分给她的房子是毛坯房,还需要装修。那时的电子邮件系统还只能处理英文,没有中文系统,我又不是很确定用英语怎么说装修这个概念,咨询了几位老师,用了refurnish and decorate,后面还加上了一个括弧(zhuang1 xiu1)。向明回信说房子里没有家具什么的都不是问题,她可以睡地板,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她回来不能马上住进新房里去。经过几次解释才算搞清楚。向明回国那天所里安排我和当时刚留校的师弟官风华一起去接机,那天北大车队说不巧所有小车都已经派出去了,只有一辆中巴可以出车。我们就坐着一辆早该报废的又旧又破的中巴车去了机场。在机场的出口外举着写有陈向明名字的纸牌等她,一会儿一位矮个微胖、穿着和气质都很不起眼的一位中年妇女从我们旁边走过来,说我是陈向明。回到学校之后,官风华私下里对我说,他感到很失望,没想到留学这么多年的哈佛博士一点儿也不洋气,说他打死也不愿出国留学了。

那是1995年的3月份。后来官风华还是出国留学并留在美国工作了。还有就是这位外表不起眼的小个子老师,回国后开设课程,开展研究,著书立说,把西方源于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的质性研究方法最早带到中国,在教育领域推广应用。也是唯一一次,使中国的教育学术在研究方法方面领先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
陈向明老师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王小刚为什么不上学了》,是她参加当时高教所承担的世界银行贫困省发展项目的重度辍学研究的调研后写成的,论文用很具体细致的笔调围绕一名初中生的辍学原因的调查访谈展开。文章里有对各方面访谈的情节环境及访谈内容的描述,有对访谈对象的表情、举动、穿着的描述,甚至还具体到作者哪一顿午饭在哪儿吃了什么饭菜。这样一篇论文与我之前看到的所有文献都极为不同,当时对我和同事们的触动都很大:研究居然可以这样做!这篇论文在我们看来更像是一篇文学作品,小说或报告文学之类的。还有一位研究生还专门发文,跟陈向明商榷她的研究究竟是质的研究还是新闻收集。当然在关注和质疑之中,向明和她的团队推广的质性研究方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响应,影响越来越大,她们每年暑假会专门面向社会开设关于质性研究方法的暑期课程,报名情况特别火爆,开课的老师们需要在申请人中做筛选,甚至不乏有人找熟人托关系来报名的情况。在教育领域,一个没有学分没有学位的课程做到这样,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陈向明的研究成果在学术圈内、特别是教师教育领域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按后来管培俊老师的话,“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认知”。现在质性研究方法在大学里开展得也越来越广,越来越多的硕士博士论文采用这种方法做研究。质性研究成了继量化研究之后在我国教育学界得到推广普及的另一种最重要的实证研究方法。
四
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电脑上写东西,闵老师进来说:晓宇,你该读博士了吧。于是我就报名参加了那年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忘了是什么原因我当时不需要考专业课,只要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英语考试。北大博士生入学的英语考试,是出了名的变态难,不过那年我考得还不错。1995年秋我顺利地入学做了在职博士生,同时作为所里的青年教师,还兼职做了高教所那年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班主任。就这样,我自己做了自己的班主任。
这个时候高教所硕士每年招生人数扩大到了5人左右,博士每年有2到3个,我们这年的三位博士生是阎凤桥、李曼丽和我,硕士班的同学有何光彩、蒋凯、邱黎强、董辉萍和彭源。我这个学生兼班主任跟同学们关系紧密,经常去研究生宿舍里聊天吃饭喝酒。当时研究生的文体活动也很活跃,在我做班主任期间高教所拿过一届硕士杯篮球赛冠军,张贵龙、董树华、萧群、蒋凯和何光彩都是那届篮球队涌现出来的主力队员,即将入学的博士生文东茅是球队教练兼陪练。在北大的几十个院系里拿到冠军,这对高教所这样的小单位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为此当时的同学老师们还专门到燕春园聚餐庆祝了一顿。
1997年我参与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工作,这个项目是陈良焜老师向教育部财务司领导建议立项的,从世界银行申请了七万美元课题经费。这项研究是北大和国家统计局城调队合作进行的,我们设计了一个关于教育的调查问卷,由国家统计局进行入户调查。调查涉及7个省市的8000个城乡家庭的28000多个个人,把教育经历和收入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计算教育收益率的样本数据,这样规模的调研和数据在20世纪90年代还不多见,能够支持比较可靠的量化研究了。用这个数据,还有后来结合1990年、1999年的数据,我跟闵维方老师、陈良焜老师分别合作,发表了几篇关于教育收益率的论文,是我早期比较像样的成果发表了。
因为我的工作内容就是做研究,博士论文的研究并不构成额外的负担,所以第三年我就做完了论文,与全日制的同学一起毕业了,这对我这个在职的博士生来说属于提前一年毕业。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叫“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研究”,后来大家统一用的概念叫成本分担,就是中国大学逐渐开始收费的改革。在博士论文研究里除了利用了教育收益率的数据之外,还有一个是我自己设计的大学在校生调研。我设计了一个大学生对教育估价以及在校经济收入和支出的问卷,主要请我做班主任的这个班的硕士研究生在学生午饭的时间到北大本科生宿舍里敲门发问卷,填好问卷的送其一支笔作为感谢。因为样本里各个年级的学生都有,而他们刚好是在学费逐年提高的背景下入学的,每个年级的学费水平都不同,我在博士论文里分析了四个年级的家庭经济收入水平的分布,最后虽然样本量还不够多,而且四个年级的数据也不是稳定一致,但大体上看出来低收入大学生逐年减少的趋势。沿着这个方向,后来我利用更大一点样本调研数据测算了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基尼系数,研究思路和方法的雏形在博士论文里已经有了。
在我论文快答辩的时候,有一天汪永铨老师到我办公室,问我论文做得怎么样,我说快完成了,之后补充了一句:其实其中的干货,也就那么一点点。汪先生带着他那一贯的微笑看看我说,有干货就好!后来在所里开会的场合,我记得老先生说了不止一次,说做研究写论文,有自己的“干货”最重要。
我的博士论文是跟阎凤桥同一天答辩通过的,答辩委员会除了我们共同的导师闵老师,还有汪永铨、陈良焜、孟明义和王善迈。答辩还是在高教所的阅览室进行的,答辩秘书是陈洪捷,他当时也是在职读博状态。在答辩合影的时候闵老师和我们站在后排,几位老先生端坐在那张大阅览桌前,王善迈老师那时候还是满头黑发。

博士毕业之后的1998年10月我去了美国做访问学者,1999年4月回国,参与了学校财务部和基金会的业务和管理工作。此后十多年,都是既做教学科研也参与党政事务,做了不少事情,也有可能耽误了不少事情。
从初进高教所读书,到今天转眼30年过去了。其间不少同行了解到我的本科专业后会问我为什么当时转行学了教育,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在每一个节点上的选择,似乎并没有太多的规划和目的性,没有太多的起伏波折,实在要总结的话可以说属于顺时势而走自己能走的路。
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初的几年是北大教育学科发展速度比较快的时期,此时队伍的规模在不断壮大,学生人数快速增加,办公空间也逐步扩大。到2000年,高教所与电教中心合并成立了教育学院,这一发展进程算是告一段落。拿到当前背景下看,在北大清华这样的大学里,一个学科想要扩大规模要难得多,对学术队伍的水平素质要求也高得多。
2020年是北大教育学科恢复40周年、教育学院成立20周年。2018年和2019年我们刚刚回顾了改革开放40周年、共和国成立70周年。今年我们可以把北大教育学科的发展放在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和教育事业发展的大背景下来看,可以说过去几十年是中国教育事业也是教育学科开拓和发展的黄金时代。从我个人的一些经历看,我有幸亲身经历和参与了一些第一次,比如前面说到的我硕士期间参与的那届“挑战杯”是北大办的首届,后来我的博士论文获评高教学会的优秀博士论文也是高教学会的首届,当时一起获奖的还有陈洪捷、阎光才、周光礼等。我们的老师和同事们在此过程中做出了不少高质量的创新研究,北大的教育学科和教育学人在学科发展与国家教育事业发展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北大教育学科在国内同行中的印象大概包括多学科和交叉学科、注重量化和质性等实证研究方法、与国际学术前沿密切对话、紧密联系政策实际等多个方面,这些特点,在90年代我在高教所先学习后工作期间均已经有所表现。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壮大,如今的北大教育学院在规模和条件上跟30年前的高教所已不可同日而语。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开始提出世界一流大学的概念,但普遍感觉那是渺茫的幻想,但今天北大清华都已经在盘算着建成世界一流的具体时点了。在有的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北大的教育学科有时也有不错的表现。教育学院、北大乃至整个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都经历了不寻常的变化。在这个不寻常的时代,能以个人的平凡际遇,见证和参与这样的奇迹,是我的人生大幸!
原文刊载于《学术之道》,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作者陈晓宇。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来源:北京大学教育学院